《入慕之宾》
作者:海青拿天鹅
简介:
一场动荡,换了皇帝,朝廷洗牌。
宫中玉清观女玄真阿黛,皇帝眼里的发小,后宫眼里的绿茶。
阿黛的日常:
嗑瓜子听后宫八卦,给嫔妃算命,听皇帝吐槽嫔妃,再收黑心钱给嫔妃们拉皇帝的皮条。
最后,跟所有人一起骂万恶之源太上皇。
千算万算,只为挨到太上皇英年早逝,皇帝掌权,天下大赦,她好带着不义之财远走高飞。
没想到,大赦之日提前来到。
太上皇没有英年早逝,但英年早婚。
他要娶的人,是她。
精彩节选:
才入三月,一场北风,让原本见暖的天气来了一场倒春寒。
雨接连下了几日,好容易有了个晴天,微风里,仍透着凉。
乐歌伴着笛声飘来,隐约可闻。
那是不远处的太乐署里,正在为皇帝的册妃典仪排演。
春风里,丝竹悠扬,带着花香,传到玉清观的亭子里来。
……这位崔贤妃,入宫也才不过半年。先是封了个采女,侍寝之后,一下就封了宝林,没几日又封了美人。后来一路晋位,做到了贤妃。前头的董淑妃,是诞下了皇子才进位,崔贤妃却只是得了孕,就马上受封。如此盛宠,可真是圣上继位以来绝无仅有。
兰馨殿的苏美人今日打扮得很是素雅,发髻堕堕,簪着绢纱堆的宫花,又平添几分可人的俏丽。她带着几位新进的宝林和采女到玉清观里烹茶闲坐,笑声琳琅,让安静的园子里显得热闹起来。
崔贤妃未出阁前,也是京中的官家闺秀,不知玄真见过她么?苏美人问道。
我手里拿着绣绷,正照着绣样,给凤凰的羽毛添上金线。
太后寝殿软榻的迎手,每年都要换一次。她最喜欢我绣的凤凰,所以每年也都由我来绣。
下个月初,就是太后四十岁的大寿,这绣品,便是我的寿礼。
倒不是我喜欢做这个,而是太后身上的用物,从手帕到鞋底,都由急于展现孝敬之心的嫔妃们包办了。我这等外人,不好喧宾夺主,也只有在迎手这等不重要的物件上显一显身手。
记不得了。我说。
崔贤妃确是生得娇艳,莫说圣上,妾等也是喜欢得很。一旁的张宝林道,听说上个月,圣上到骊山的汤泉宫曲,点了崔贤妃侍驾。她戴了一顶金莲冠,见到的人都说,颇有玄真之风……
一根金线绣歪了。啧。
大约是察觉到我的眉头皱了一下,苏美人轻咳一声,张宝林忙噤声。
宫里人多了,难免有那喜欢胡说八道乱嚼舌根的。苏美人话语轻柔,道,谁不知道太后疼爱玄真,有人爱投机取巧,也自不稀奇。
说罢,她将一杯烹好的茶端到我的面前:天底下莲冠戴得好看的人多了去了,可正如太后所言,唯有那心怀道法之人,才能真配得上。不然,就算是再像,也不过是东施效颦罢了。
张宝林忙讪讪附和道:苏姊姊所言甚是。
话音落下,无人接上。
不远处,几个采女正在一树海棠下采摘绽放的花朵,插在发髻和鬓间。嬉闹的笑声,如莺啼般婉转,更显得亭子里安静。
我仔细地盯着绣绷,好一会,才终于将它拆下来。
抬眼看了看苏美人,我微微一笑。
好些日子不曾见美人了。我说,听说,美人近来颇得中宫赏识,日日在昭阳宫中用事?
苏美人的脸上浮起一丝尴尬,旋即闪过不见。
她神色谦恭:妾小小宫嫔,哪里堪得中宫大用。只不过是中宫出了正月就到隆福寺礼佛去了,无暇处置宫中事务,见妾粗通文墨算数,便将妾召到昭阳宫里去帮忙。
说罢,她转头朝身后的宫人看一眼。
那宫人随即上前,奉上一只精巧的漆匣。
妾这些日子事务缠身,无暇到老君前进奉,心中着实愧疚。苏美人一脸诚恳,对我道,这些银子,权作香油,还请玄真收下,供奉神仙,以表妾虔诚之心。
美人有心。我说,只是这殿上的香油,也着实费不得许多银子。
苏美人忙道:玄真和一众女冠日日念经供奉,也总是辛苦。如今方才开春,观中总要修葺,也要添置四季衣物。剩下的,也仍是妾的心意,还请玄真笑纳。
我念了一声无量寿福,道:如此,多谢美人。
身边的小道姑兰音儿听得这话,随即上前,将漆匣接了。
又寒暄了一番,苏美人起身告辞。
我放下绣绷,起身送她。
才出亭子不远,苏美人忽而道:妾听闻,太上皇要回来了,也不知确否?
脚步定了一下。
贫道不曾听闻。我随即道。
苏美人露出苦恼之色,道:上次太上皇回来,圣上便到大营里练兵,足足两个月也不见人。我等嫔妃,本就难得轮到见圣上一面,隔着这许多日子,也不知圣上还能不能记得妾是什么模样。
我望了望前方开得正盛的梨花。
后日,圣上要陪太后到玉清观来赏梨花。贫道听闻美人烹茶甚妙,何不到时候过来,为太后和圣上一展茶艺?
苏美人眉间一喜,笑盈盈地一礼:恭敬不如从命,多谢玄真。
我抖了抖拂尘,拱手胸前,款款一礼:无量寿福。
回到亭子里,兰音儿正看着匣子里的东西,叹道:我粗粗掂量掂量,少说也有五十两。玄真,这些宫嫔怎一个个似财神似的,出手就这般阔绰?这香油钱,便是乡下的殷实人家,也足够一大家子人过一年了。
我说:苏美人母家虽非名门望族,却也是河东大户,世代为官。这点银两于她而言,比九牛一毛还不足挂齿。
说着,我看了看那漆匣里的银两,确有不少。
都充公吧。我说,不久便要入夏,给观中众人置办些岁时衣物,剩下的都平分了,也好让各人手里攒些体己。
兰音儿笑嘻嘻:就知道玄真对我们好。
说罢,她收了银子,喜滋滋地跑开了。
我轻轻晃着手里的拂尘,信步离开杏花盛开的园子,往外头而去。太乐署的乐声又起,这一次,虽也是雅乐,却并非册立后宫所用,而是一支熟悉的曲子。
入阵曲。
当今天下,宫里宫外,上至皇帝太后,下至平民庶人,能用此乐的,只有一人。
我咬了咬唇,加快脚步。
我叫上官黛,是宫中玉清观的住持。
玉清观位于皇宫一角。今上的祖父穆皇帝笃信黄老之学,后宫之中也崇拜此道。为了方便后妃们拜神念经,穆皇帝就在御花园之中设下了这道观。
先帝是个爱好展示武德的人,厉兵秣马,雄心勃勃。当年北戎连年遭遇大旱,实力大减。先帝认为那是消灭北戎的好时机,力排众议,亲率二十万大军出征。
可天有不测风云,一场大雪突然袭来,将大军困在了半路。而原本仓皇撤退的北戎回过神来,利用熟悉的天时地利一举反攻。
这一场大战,以先帝惨败收场。
先帝被北戎所俘,麾下的二十万王师全军覆没,或死于风雪,或被北戎所杀。
其中,包括了我的父亲,郑国公、左相上官维。
他因护萧先帝而战死,连尸首也不知下落。噩耗传来,我家上下悲痛欲绝,接着,却听到了更大的噩耗。
乱作一团的朝廷,并没有因为先帝被俘而同仇敌忾,反而加剧了平日就已经十分尖锐的党争。毕竟没有了天子,朝廷中谁可做主,就变得格外重要。
这场争斗的结果很快出来,我那曾经位极人臣的父亲,死后背下了所有的黑锅。
他们总不能追究先帝的罪责,便说先帝亲征是上官维怂恿的,罪大恶极。
接下来的事,便是水到渠成。郑国公府被抄,男子流放,女子为婢。
我的祖父祖母早已经去世,我的母亲体弱,也在我小时候撒手人寰。故而被治罪的,除了兄长上官谚和我、三个年幼的庶出弟妹,便剩下了父亲的四房妾侍。
有时,我会想,可怜她们刚刚失了丈夫便要被卖为奴婢。若是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,也不知她们还会不会每日争风吃醋,斗得鸡犬不宁。
我被送入女牢,在寒冬腊月里做了三个月的洗衣婢。突然有一日,我被人提出来,说要让我到宫里的玉清观出家。
此事的缘由,要从当时的朝廷格局说起。
在我做洗衣婢的三个月里,朝廷里的争斗,终于有了一点结果。御史中丞耿清和赵王一道当上了监国大臣,成了朝廷主事。
耿清此人颇为忠直,连我那跟他属于政敌的父亲也曾这般承认。
但就算是他那样的忠直之人,也不免有些迷信,容易病急乱投医。
当时,朝廷为了从北戎手里迎回先帝,可谓是绞尽脑汁,焦头烂额。这耿清也不知在哪个方士那里算了一卦,说上官维的女儿不能下狱,而是该到宫中的玉清观出家,供奉神仙,方能让先帝化险为夷。
于是,耿清力排众议,将我送进了玉清观,做了个女道士,法号玄真。
后来,耿清力主迎立齐王为新君,被政敌暗杀。
齐王则为他报了仇,登基之后,在京中立了祠。
这是后话。
直到现在,我仍记得抄家那日,我被人拽走,回头望见兄长上官谚正被人绑着,押出大门。
我一边哭着,一边大声叫着他。
兄长平日里待我总是严厉,不但总查看我功课,还教训我不可任性,此时,却只定定站在那里看着我,别人推搡也不走。
隔得太远,我听不清他说的话。
我想着,他也许是像从前我入宫时那样,嘱咐我要听话,不要生事。
那之后,我再也没有见过任何的家人。
只听宫里消息灵通的人说,因得我父亲上官维的罪名多少有些争议,朝廷倒是没有下死手族诛。除了我父亲这一支,别的叔伯族人幸免于难。
我那庶出的弟妹们,虽然还年幼,却还是入了奴籍。据说,落罪之后没多久,他们就被人买走了。至于卖去了哪里,无人知晓。因得那年动乱。执掌此事的官署被大火烧毁,记载他们下落的契书籍册,也随着动乱灰飞烟灭。
唯一有音讯的,是我的兄长上官谚。
他被流放到了辽东戍边。那个地方,据说每年入秋就已经冷得很,冬天下一场雪就会冻死不少人。
话说回来,也不知是不是我到玉清观里出家果真灵验。一年之后,北戎竟把先帝放回来了。
不过在这之前,朝廷已经有了新的皇帝。
上官家倒台之后,朝中的争斗并没有因为有人被治罪而停止。毕竟先帝在北戎那里当了俘虏,而这边,国不可一日无君。
要不要另立新君?立谁为新君?
每一点都足够让人争得你死我活。
几个皇子更是倚仗背后支持的势力大打出手,闹得烽烟四起,民人流散。
而结束这一切的,是一个谁也没想到的人。
先帝的弟弟,如今的太上皇,齐王景曜。
往事如同天上的浮云,将太阳的光辉遮去,在心中留下阴翳。
我深吸一口气,将杂念抛开,继续沿着石子铺就的小径,来到御苑边上的紫云楼里。
你来迟了。
一个声音忽而从身后传来。
我转头看去,一人倚坐在楼边的美人靠上,手里拿着一壶酒。
景璘看着我,似乎对吓我一跳很是满意,脸上带着那不羁的笑。
他身上穿着常服,脚上的织金龙纹履却没有换。
显然,他刚刚散朝。
陛下。我也露出微笑,行了个礼。
景璘是当今皇帝。
不过除了明面上,他管他自己叫朕,我从直呼其名改成称他为陛下,其他并没有别的改变。
景璘指了指美人靠的另一边,让我坐下。
这么迟才来,朕那些嫔妃,又找你去了?他自斟自酌地喝一口酒,漫不经心道。
苏美人和张宝林带着几个新入宫的采女过来,拜拜老君,再陪我坐下来喝喝茶。我说。
苏美人?景璘露出迷茫之色。
我说:便是去年年末才入宫的,益州刺史苏律的侄女。
景璘想了想,好一会,终于哦一声,道:那个胸大的。
我:……
景璘笑了笑,一脸无辜:母后每个月都往宫里塞人,朕连谁是谁都分不清,能记住这些不错了。
说罢,他拿起酒壶,倒了一杯酒递给我:岭南去年进贡的琥珀春,朕一直收着,今日才想起来尝一尝。来一杯?
我接过那杯子,尝一口。
这是烧酒,比我平日自酿的浓烈许多。
我皱起眉头,嫌弃道:陛下不久前才得过风寒,太医说过不能饮酒。
太医院那些老儿知道什么,整日这不能吃那不能吃,若是听他们的,朕只好吃糠。
我看着他:你就不怕我告诉太后?
你敢!景璘即刻瞪起眼睛,你若告状,朕就说你不守清规,私自藏酒!
那气呼呼的样子,与少年打闹的时候并无二致。
我笑了笑。
苏美人找你何事?景璘道。
她给我送了五十两银子,说是香油钱。她手艺极好,我邀她后日到梨花宴上去,为陛下和太后烹茶。
景璘颔首,大方道:日后再有人给你塞银子你收着便是,不必禀报。
我看着他,叹口气:如今后宫里都说,崔氏能当上贤妃,都是我巧言令色游说而来。
不是么?景璘反问,不是你说她父亲崔如海在南边镇守,颇有建树,是个能臣。朕正当用人之时,要对崔家施以恩惠?
但我可不曾让陛下一下将她封为贤妃。我说,陛下难道不怕别人说陛下偏听偏信,是个任人耍弄的傻瓜?
他伸个懒腰,笑得愈发贱兮兮:那要看如何弄,朕也不是什么姿势都喜欢的。
我翻个白眼。
放心好了。景璘道,天下人从来不真讨厌傻瓜,只讨厌不好糊弄之人。朕越像个老好人,喜欢朕的人越多。下次听到谁嚼朕的舌根,就直接告诉朕,朕将他们舌头割了。
我看着他:陛下找我来,所为何事?
没事就不能找你么?景璘仰头灌一口酒,沉默片刻,忽而道,太上皇要回来了。
我说:我听到了入阵曲。他何时回来?回来做什么?
下个月就回,谁知道他要做什么,景璘哼一声,目光中却没有了先前的随意,朕该去大营观兵么?
我沉吟片刻。
不去为好。我摇头,道,陛下既然在他面前示弱了三年,还是继续示弱下去为好。贸然观兵,只会让有心人浮想联翩,于大局不利。
景璘颔首,轻轻转着酒杯:朕也是此想。
说着,突然,那精巧的瓷杯从他手中狠狠掷出,摔到了紫云楼下的石阶上,登时粉碎。
你说,景璘坐了起来,一脸忿忿,他一个宗室,居然敢与朕争天下!他是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?
这个问题,有且只有一个答案。
是,他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我笃定道。
景璘看着我,再度露出满意的笑容。
阿黛,他又喝一口酒,叹口气,许多话,朕只敢跟你说。
我也喝一口酒,苦笑:我何尝不是。
我和景璘,自穿开裆裤之时,就已经玩在了一起。
在京城里,上官家的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,四世三卿,真正的高门大户。我的父亲上官维,是本朝最年轻的宰相。
这样的人家,很自然会被皇家看重。所以,我的姑母上官娴,在十六岁的时候入了宫,没多久,就因为得孕,封了贵妃。
我听家里的老人说,那时候,没有人怀疑,姑母如果能生下皇子,那么一定能当上皇后。
事情如所有人盼望,姑母顺利得了孕,太医都断言,那定然是个皇子。
但老天终究开了个玩笑,她遭遇了难产,不但孩子没了,自己还了丢了性命。
所幸先帝是个情种,因得对姑母的眷恋,他对上官家不错。
从小,我就能入宫去玩。只要宫门没有落钥,我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。要是不想回家,我也能宿在宫里。
当年的龚昭仪,也就是今日的太后,跟我姑母是义结金兰的姊妹。我每次留宿,都是在她的宫里。
也是因得如此,我和景璘关系匪浅。
宫人们常常开玩笑,说七皇子日后长大了,就娶了上官家的小女君吧。
但这并不是我父亲上官维的打算。
在他看来,上官家虽然已经位极人臣,但还不够。如果能再出一位皇后,跟皇家的关系更紧密一些,才能长久地荫蔽子孙。
所以,在我姑母去世之后,这大任落在了我的身上。
父亲为我相中的夫婿,是当时的太子。
太子是王皇后所生。
王皇后早逝,先帝迟迟没有立后,但把她的儿子立为了太子。
为了达成目的,父亲与王皇后的兄长王国舅来往甚密。不过这太子着实不争气,小小年纪就学会了轻慢大臣,刚愎自用,还学会了结党营私。
先帝一怒之下,就将他废了,并且再也没有立太子。后面先帝被俘,朝中因为没有太子而引发了诸皇子作乱,也是因此埋下的祸根。
我不喜欢太子,作为玩伴,我更喜欢景璘。
他只比我大三个月,可谓臭味相投。无论是捉弄宫学里的同窗,还是逃课玩耍,或者是捉住之后受罚,二人都坚定不移地同舟共济,狼狈为奸。
那快乐的日子,一直持续到先帝被俘。
景璘是七皇子,虽然排行小,也时常闯祸,却颇得先帝的喜爱。
许多人猜测,那是因为他母亲和我那死去的姑母关系好,先帝爱屋及乌。
于是亲征之时,先帝带上了他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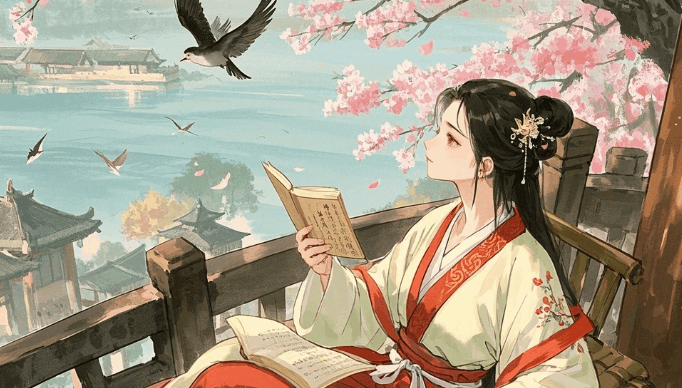
这事,面上的说法,是要历练皇子,开拓见识。但每个人都知道,这是先帝偏心,想借亲征之事,给这七皇子积累资历。
还有许多人猜测,等先帝亲征回来,说不定就会立龚昭仪为皇后,七皇子则顺理成章地立为太子。
我也这么盼着。
虽然我对当皇后毫无兴趣,但能有一个当皇帝的发小,是再好不过的事。
可惜天有不测风云。
先帝被俘,景璘也跟先帝一道,做了北戎的阶下囚。
幸好时间不长,只有一年。
但一年里,足够发生许多事。
北戎没有杀先帝和景璘,而是留着他们,向中原勒索财物。
而我,虽然入宫做了玉清观的道姑,暂且逃离了被卖为官奴的火坑,却也没有过得多好。
因得诸皇子争位,京城数度陷入夺宫大战。宫中昔日尊贵的嫔妃和皇子皇女,都惶惶不可终日,甚至为了躲避战乱仓皇逃窜,颠沛流离。
那时,我在宫中能依靠的,只有龚昭仪。
龚昭仪失了丈夫和儿子,我没了全家。
她曾对我说,她知道上官家是冤枉的。
因为这句话,我在听闻叛军进了京城的时候,当机立断,劝她跟着自己一起逃出宫去。
我虽是个罪臣之女,可玉清观毕竟是个皇宫里的道观,值钱东西不少。当时的住持娘子待我不错,教了我不少道理。可她已经重病缠身,时日无多,实在跑不动了,就让我将一些值钱物件带上,自己逃命。
我用那些财物贿赂了管马厩的太监以及宫门的守卫,得了两辆马车和几匹马,然后,带着龚昭仪离开了皇宫。
不久之后,我听说皇宫被叛军攻破,来不及逃走的人受了一场屠戮。
我的父亲在终南山中有一处消暑的别墅,景色美丽,但人迹罕至。自上官家倒了之后,这别墅也随之废弃,连道路也长起了野草,几乎找不到了。在战乱之时,这是个绝佳的藏身之处。
于是,我带着龚昭仪及随行太监宫人躲到了这里。听得宫里的惨状,众人又是惊惧又是庆幸,可更多的,是担忧。
毕竟如果这动乱一直持续,我们就算跑得再远,也是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。一群阉人和妇人,不会刀不会枪,身上还有细软,随随便便一伙土匪就能把所有人祸害干净。
我们哪里也不敢去,深居简出,在山中提心吊胆,度日如年。就在众人都觉得我们不久就会完蛋的时候,有一天,一个消息从京中传来。
先帝最小的弟弟齐王自青州起兵,一路势如破竹。
几个皇子割据四方,正打得火热,没想到背后杀出个程咬金来。
起初,没有人将齐王这区区宗室放在眼里,不料,齐王竟是各个击破,一举平定了战乱。
自乱事开始,天下人无不盼着能有个天降的神仙来涤荡尘埃,还世间太平。
如今,齐王做到了,他就成了那个天下归心的神仙。
接下来,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争执的事情上。
国中无君,谁来当皇帝。
自然有人主张攻打北戎,迎回先帝。但且不说经过那场大战和后面的动乱,中原已经元气大伤,就算能再拉起大军,此计也不可行。先帝是北戎的人质,若战事再起,北戎会不会败不说,先帝只怕要性命难保。
若不能迎回先帝,便只有另立新君。
先帝的几个皇子作乱,天怒人怨,自无人支持。
而齐王身为平叛的功臣,人心所向的天神,自然而然地成了那继位人选。
于是,他顺理成章地登基为君。
齐王登基之后,发布安民诏书,令重整各处官衙,惩治作乱贼人,平抑物价,重开贸易等等。
其中还有一条,先前逃亡宫人可返回宫中,重新安顿。
一名太监偷偷从附近城镇里将告示抄了带回来,龚昭仪看了,一夜未眠。
第二日,龚昭仪告诉我,她要回宫。
我知道,这是龚昭仪唯一的选择。
她和周围的这些太监宫人,都是在宫中生活多年的,那个地方再怎么样吃人,也是他们赖以生存之所。山里的苦日子虽不长,但足够让他们怀念宫中的丰衣足食。
至于自己么……
我只想等局势太平之后,到辽东去找我的兄长。就算在路上被饿死冻死,也好过留在京城,看朝廷里那些让我家万劫不复的所谓人上人的嘴脸。
但太监还带来了另一个消息。
已经成为新帝的齐王,将远在北戎的先帝尊为太上皇。
也就是说,先帝还活着。
龚昭仪特地将我叫到跟前。
她问我,难道你不想为父兄洗脱冤屈,而甘心做一个逃犯么?
我也一夜未眠。
我知道,自己并不甘心。
于龚昭仪而言,先帝没死,景璘就可能也没死。齐王要在面上维持对先帝的尊敬,必然要善待他的嫔妃,尤其是龚昭仪这样仍有皇子留在先帝身边的嫔妃。
于我而言,我家的罪因先帝落下,自然也只有先帝可解。我就算找到兄长,也不能让他除罪获释,那么最好的路子,仍然求先帝为上官家脱罪。
第二日,我睁着泛青的眼睛,对龚昭仪说,我会跟她回宫。
唯一让所有人都感到难以捉摸的,其实是齐王。
这位齐王,其实在平乱之前,便已经是闻名天下多年的人物。
因为他长得好。
——
齐王名叫景曜,是先帝最小的弟弟,穆皇帝最小的儿子。
他生母是一位宫人,和我母亲一样,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。
那时,穆皇帝因为笃信神仙,常年服用丹药,已经病入膏肓。幼子的出生,让他认为这是大吉之兆,欣喜之下,直接打破皇子成年才封王的规制,将婴儿封了齐王。
可惜这喜事终究没能给穆皇帝续命太久。数月之后,穆皇帝驾崩,新皇继位,便是先帝。
对于这个弟弟,先帝并没有许多关怀,因为年幼,也没有给他开府,而是将他送到了京郊的同春园里。
同春园是一处皇家苑囿,大得很,宫室众多。
齐王住的宫室,叫清澜殿,在同春园的一角。宫中每月仍照皇子定例奉养,除此之外,先帝似乎就把他忘了。
不过,齐王这个人,似乎天然不会因为别人不理会而埋没。
许多年后,先帝四十大寿。
先帝喜欢漂亮场面,于是从朝廷衙门到王公贵族,无不绞尽脑汁,力求大庆。
同春园附近有开阔的草场,于是宫中仿六礼之制,比赛射御。
这场比赛,办得很是盛大,京中但凡有点头脸的门户,都派出家中的男子参加,只图在先帝面前露露脸。
场面据说很是激烈,不过谁也没想到,全京城的官宦贵胄子弟,包括太子,都败在了一个人的手下。
那个人不是别人,正是十五岁的齐王。
这场比赛,我不在场。
因为我最讨厌的就是贵胄们云集的场面。
父亲总要求我像个大家闺秀,不许我有一丝松懈。
所以,伺候我的仆妇给我梳头发的时候,会用力梳得紧紧的,还要戴上精致沉重的发饰,扯得头皮生疼;身上要穿上华丽的衣裳,衣带箍得紧实,莲步慢行;要细声细气说话,脸上永远保持谦恭端着之态,还要记住那些乱七八糟的贵胄家眷,谁是哪家的,叫什么名字,一个人也不能叫错……
我觉得,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无聊的事么?留在家里睡觉也比受那活罪强。
所以那日,我照例说不舒服,待在了家里。
于是,我错过了京城之中被热议最久的场面。
射御优秀的人,天底下从来不缺。只是这样的人,一般不会出现在养尊处优的贵胄之中,也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,公然抢了太子的风头。
据我的闺中好友们事后说,当时,太子大约立志要在皇帝和群臣面前露一露脸,穿得似只花孔雀一般,得意洋洋。
子弟们都是识时务的,不是射箭时失了的,就是御马时跑得慢,让太子一骑绝尘,远远领先。
但谁也没料到,一个少年杀将出来。
他十射十中,还骑马跑得飞快,让胯下坐着一匹汗血宝马的太子在后头吃了一脸的土。
全场震惊,没有人想到竟然出了这等变故。
人们或好奇或兴奋地议论纷纷,猜测那胆敢如此不懂事的少年是谁。
而当少年终于骑马来到看台前的时候,众人再一次被震惊。
倒不是因为太监报上了齐王的名号,而是谁也没想到,那几乎已经没人记得的齐王,竟是这般俊美的少年。
我的闺中好友们一脸陶醉地说,齐王站在玉阶之上,就像头顶的阳光一样,熠熠生辉,所有人都有那么一瞬的失神。
当时听着这话,我不以为然地说,搞不好那齐王头顶上真点了一盏灯。
她们无语地看着我,随即群起而攻之。
一番教训之后,一人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等你自己见到了,就知道我们说的是不是真的。
话说到此处,那就没什么退路了。
我是个从不肯认输的人,哪怕是浑身上下只剩嘴硬,我也会让嘴硬得像铁打的。
虽然没多久,我真的在宫里见到了齐王,也真的像她们说的那样,愣了一下。
我承认,纵然我见过许多美人,也不曾见过齐王这样的。
白衣少年,美而张扬。
他高傲地站在那里,将周围所有人都变成了陪衬,与讲究面上和气的宫廷格格不入。
当时,我的兄长上官谚正在跟他说话。
兄长是个喜好结交的人,自然不会错过齐王。他见我来,招手让我过去,对齐王说,这是他的妹妹,小名阿黛。
我走过去,行个礼,脸上堆起京中闺秀见人时那甜美又不失端庄的假笑。
可齐王之看了我一眼,只微微颔首,便继续跟兄长说话去了,视我如无物。
天地良心。
我倚仗着先帝的厚爱,自幼出入宫廷,无论宫内宫外,只有我不想搭理的,绝无敢不搭理我的。哪怕是皇子公主们,遇到我,也总要说上些话。
头一次被人如此漠视,我的脸黑下来,心头刚刚浮起的一点涟漪也已然荡然无存。
我的好友们听闻我见到了齐王,马上赶来我家里问我观感如何。
看着她们期待的脸,我也高傲地昂着头,更加不屑:哪里好了,不过徒有其表。
她们一脸唾弃,说我朽木不可雕。
但显然,先帝跟我想的一样。
齐王突然现身,抢了太子风头,太子自是很不满。
先帝虽然不喜欢太子,但他也很是不满。
毕竟太子再不成器,那也是他的太子。
齐王拂了太子的面子,那就拂了先帝的面子。
面上,碍于孝悌,先帝对齐王很是嘉许。
在齐王赢了那场射御之后,先帝亲自给齐王赐了御酒和金帛。但宗室的人为齐王奏请开府之事,先帝却置之不理,仍让齐王待在那偏僻的行宫之中。宫中的节庆宴席,也仍然没有齐王的份。
然而齐王在京中掀起的热潮却是有增无减。
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,谁能拒绝讨论一个少年俊美又行事不羁的亲王呢?
在不久之后,另一件事,让齐王一举封神。
吐蕃来朝。
作为西陲之国,吐蕃与本朝的关系一向微妙,交锋数次,互有胜负。当下虽相安无事,却也不妨碍明里暗里的小争斗。
包括马毬。
马毬在本朝很是风靡,无论士庶贵胄,是男是女,都热衷于此。
而吐蕃人生来彪悍,亦长于此道。每回来朝,他们都要带上些马毬好手,与天朝贵胄子弟赛上一场。
这次之前,本朝雄风不振,已经连续三年败于吐蕃,堪称奇耻大辱。
果然,这一回,开局之后,也打得很不好看。
吐蕃人连进数毬,看台上乌泱泱的观众一脸丧气,先帝的脸也有些挂不住。
然后,齐王自请上场。
众目睽睽之下,他骑着一匹白额栗马,风驰电掣地从吐蕃人手中抢了毬,而后,轻松破阵,击毬入门。
在众人欢呼之时,场上形势一举逆转。齐王以一己之力连进数毬,将吐蕃人硬是打得抬不起头来。
计时的滴漏落尽,天朝反转,大胜吐蕃。
此事,让齐王一战封神。
就连他骑的那匹平平无奇的白额栗马,也从此有了名字,叫雪落琥珀。
至此,我的闺中好友们已然全身心拜倒在了齐王的石榴裤下,提到他就双手捧心,一脸春色。
只有我,仍旧翻白眼。
自那之后,先帝也不好在众目睽睽之中无视齐王,将他接出同春园,给他开了府。
不过没到一年,先帝就又顺手给他落实了封地,让他离京就国去了。
我仍记得那日,阴雨连绵。
比天气更阴沉的,是我那些闺中好友们的脸。她们跑到城楼上,目送齐王远去的车马仪仗,然后来到我家里抱头痛哭,顺便把我偷偷藏在在床底的一小坛梨花春喝了。
她们悲愤发誓,等长大了之后,她们要去临淄找齐王,要嫁给他。
我只得附和说,好好好。
可惜她们想得太美。女子在嫁人这件事上,无论出身大户人家还是小户人家,其实都没有什么做主的余地。她们那时都已经到了及笄之年,果然,没多久,就纷纷许了人。
只有我,因为父亲一心想盼着我嫁入宫中,拒绝了所有的媒人,让我一直待字闺中。
直到有朝一日,天塌了下来。
没有人想到,齐王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出现在了京城。京中的人,无论喜欢他的还是不喜欢他的,不仅要向他跪拜,还要称呼他为圣上。
更没人想到,他当上皇帝之后不久,又成了太上皇。
因为景璘回来了。
齐王登基之后,天下归心,迅速恢复元气。
但北戎并不愿见到中原安定。
于是,他们把先帝和景璘放了回来。
先帝在朝中仍有许多旧臣,就算齐王已经登基,在许多人眼里他也仍旧有那么些名不正言不顺,迎回先帝的呼声一直没有断绝。
现在,先帝回来了,朝中迅速分成了两派。一派要拥立复辟,一派要维持现状。
所有人都忧心忡忡,将目光盯着齐王。因为他的任何举动,都有可能让天下再度陷入混乱。
但齐王再度出乎了所有人意料。
他自愿禅位,迎回先帝。
这自然让拥护齐王的人感到失望,却让绝大多数人都松了一口气。因为此举十分符合礼制,也最大程度避免了乱事,甚至让许多原来不待见齐王的人,也出来称赞他是贤王。
不过乐极生悲,在归途之中,先帝驾崩了。
这一年来,先帝每日都在忧心和悔恨之中度过,以为返回中原无望,积郁成疾。
而齐王禅位迎他回去的消息传来,让先帝如同一个油尽灯枯之人,突然得了一剂猛药,精神焕发。见到来迎接自己的旧臣之后,先帝更是高兴,与他们抱头痛哭,饮了一夜的酒。
那之后,先帝一病不起,在离他心心念念的京城还有百余里的时候,支撑不住,驾崩了。
扶灵回来的,是一直在北戎陪伴先帝的景璘。临终之前,先帝亲手写下圣旨,将景璘立为储君。
齐王没有食言,以君王之礼安葬先帝,并迎立景璘为新帝。
而景璘则投桃报李,将齐王尊为太上皇。
至此,叔慈侄孝,北戎奸计破产,天下再度迎来大定。
关于景璘为何要将齐王尊为太上皇,说法不少。
大多数人自是称赞此乃尧舜之德,伦常典范。
不过背后的一切并没有那么简单。
齐王虽然让出了皇位,却没有让出兵权。朝廷里,也并不是景璘的天下,各处要职,大多由齐王的人担任。景璘的任何旨意都能以皇帝名义行使,不过那是在齐王无异议的前提之下。如果齐王不同意,那么就算只是放个屁也不行。
按景璘的话说,他不过是一只太上皇豢养在笼子里的鸟儿,用线操纵的傀儡。
齐王当上太上皇之后,一直住在洛阳的紫微宫里。
虽然离得远,虽然看上去,长安的朝廷在皇帝手里,可兵权却仍旧在太上皇的手上。,大到朝廷军机要务,小到地方发牢骚的折子,都是先经了太上皇的手,才会送到长安的皇宫里来。
宫里的每个人都知道,真正的朝廷,不是在长安,而在洛阳。
故而在面上,景璘对太上皇尊敬有加,将他供得高高;在心里,他则无时无刻不盼着太上皇喝水时噎死,骑马时摔死。
我虽不至于如此,但于情于理,我和景璘都是一条船的。
就在景璘登基之后,我收到了兄长上官谚托人从辽东辗转带回来的信。
那皱巴巴的信纸上,他的笔迹依旧漂亮。
他告诉我,不必为他担心,他还活着,过得也还好。
收到信之后,我只觉长出一口气,心中的大石终于落下。
如今,我唯一的心愿,是洗刷上官家所有的冤屈,让自己和兄长脱罪。
景璘是皇帝,他乐意帮忙。
这两年,兄长写来的信,纸墨越来越好,可见景璘确实是出了力的。
只是上官家的案子,早已经坐实钉死。景璘继位之后,数度要重新审理,却遭遇重重阻挠,动弹不得。当年主张将上官家治罪的人,不会容许上官家再翻身,而太上皇当政之后,他们无一不是墙头草,早早就拜倒在了太上皇的脚下。
所以,要脱罪,这些人不可不除。
至于太上皇。
景璘的敌人,便也是我的敌人,包括太上皇。
相关标签: